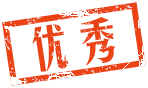|
石板坡,十字口食堂。 三十年前,妈妈牵着我和哥哥的手,给我们买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甜米饭。那是何种滋味呀,香甜的沁人心脾,以至于让我们忘了站在桌子边看着我们两个馋猫的面带微笑的妈妈。 妈妈没有吃一口。我不饿。她说。 一碗甜米饭,我们哥俩并没有吃饱。当最后一粒米下肚,我对妈妈说:妈妈,咱们再买一碗吧,好吗?妈妈窸窸窣窣地翻遍了口袋,只找到二两粮票。 下次吧,下次再吃好吗?妈妈说。 哥哥拽着我的手,说:走吧,咱们以后再吃。可我明白,一年难得吃一回甜米饭,或许以后再没机会吃了。 带着一丝遗憾与恋恋不舍的心情,我们三个离开了十字口食堂。临回头看看石板坡上矗立的食堂与三三两两的食客,我全然不知妈妈还饿着肚子。 这之后的几年里,妈妈时常带我们去那个食堂,我和哥哥可以每人拥有一碗甜米饭,而母亲总是站在桌边看着我们风卷残云。 父亲去世了,他决绝地抛下哥哥姐姐和我。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十几亩土地没有撂荒,妈妈用她单薄的身体苦苦支撑着这个家。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进过十字口食堂,再没吃过那香甜的甜米饭,直到石板坡拆迁改建,那种甜蜜的滋味默默地封存在心底。 妈妈守寡至今,我们眼看着她青丝变成白发。儿子长大了,有了出息,每次回家都嚷嚷着要吃甜米饭。妈妈微笑着走进厨房,淘米,蒸米,炒汁,加上大瓣的核桃仁红枣花生,不一会儿功夫,香喷喷的甜米饭就端上了桌。 还是那么香甜,还是儿时的滋味。母亲一如既往地站在桌边看着我吃,吃吧,我不饿。她说。 收拾完狼藉杯盘,母亲走进厨房将碗里残存的甜米饭用筷子夹起来吃掉,她舍不得浪费每一粒米。 我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为年少时的无知,为曾经失去的美好。 每次离开家的时候,我总要给她留下一些钱。妈,别舍不得,咱现在啥都不缺。我说。妈妈微笑着说:我还缺个儿媳妇。 我没让妈妈失望。我结婚的那天妈妈笑得特别开心,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妻子原本不爱吃甜食,在我的怂恿下她尝试着吃妈妈做的甜米饭,几回之后,她吃上了瘾,主动走进厨房要学手艺。妈妈的甜米饭没有失传,为此我感到欣慰。 在外的应酬多了,收入没有高多少,血压血脂血糖一个比一个高。遵照大夫的吩咐,管住嘴,放开腿,甜米饭是不敢吃了。每次回家,不等我开口,妈妈就端来一碗香甜的甜米饭。我不想给她说关于三高的话题,我怕她担心。为了不让她失望,虽然浅尝辄止,我还要吃几口,就说已经吃饱了,然后躲进书房吃降糖药。 你现在饭量比以前差远了。妈妈说。 是啊,你看我啤酒肚都出来了。我撩起衣襟让妈妈看。 你又不胖。妈妈说。 你真想把我当小猪喂呀。我说。 妈妈笑了,我真想亲吻她眼角那美丽的皱纹。 妈妈老了,她佝偻着的躯体日渐加深了亲近土地的欲望,但我希望她一直活着,给我做那香甜的甜米饭。 记忆中石板坡,十字口食堂,还有永远定格在三十年前的妈妈的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