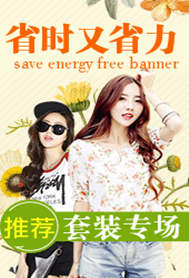 多年前看《茶经》,在“八之出”篇章中读到“山南以峡州(大约为今宜昌)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大约为今安康)、梁州(大约为今汉中)又下”时,心中很不是滋味:“茶圣”陆羽竟然将汉中乃至陕南视为最差的茶区!以致我在推介家乡名茶时始终不敢提《茶经》,而且汉中茶商也多有此难言之痛。显然,《茶经》使“汉茶”品牌陷入了窘境,让我多年耿耿于怀有口难辩。最近,笔者无意间浏览到台湾学者刘昭民的《中国历代气候变迁大势》,眼前不由一亮,多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终于有了突破口,于是顺藤摸瓜搜集了相关资料,发现只要通过抽丝剥茧,便可破解重围。 9 c, W; P0 F7 t' i+ J i, ]! o
: i1 t' ^5 {& R7 y& g' k “茶圣”陆羽(约733-804年)生于湖北天门,稍晚于“诗圣”杜甫(公元712-770年)时代,公元760年(唐玄宗晚年“安史之乱”中)于浙江吴兴著述《茶经》。《茶经》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显然,茶圣“金州、梁州又下”的观点是以当时气候条件下的物产为依据的。那么当时的气候和当前有多大区别呢? 2 Y/ O+ \$ V% ^8 g4 K
( O( `& b6 w+ Q6 u
竺可桢先生是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开山祖师,他认为隋唐时代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处于第三个暖期,对此学界普遍认可。刘昭民先生还对此暖期界定为公元600-985年,《茶经》成书年代刚好为此暖期的顶峰期。当时西安种植有大量柑橘(今天柑橘的“北极”产区为汉中),公元751年皇宫中柑橘结实;并种植有梅花和竹子,且在西安和凤翔还设立有“竹监司”。另据学者倪根金研究,唐代黄河流域普遍开发了水稻田。因此,物候专家普遍认为,唐代年平均气温平均比现在高1度左右(不过当时没有因城市“热岛效应”而形成的极端高温)。此外,从唐代女子坦胸露背的纱衫和流行的木屐,北方不耐热游牧民族的较少南犯等史实也可看出当时的炎热。 . ]! E$ m/ K' q3 N4 Q j9 I" f$ O' y
8 q9 O4 m' P4 V" J 其次,自古清泉配佳茗,囿于当时的交通和技术条件,笔者认为陆羽在评茶时只能是就地取水,这无疑将水的因素附加到了茶中。陆羽在评茶时虽也鉴水,但仅凭口鼻等感官的鉴定力无疑是非常有限的。汉中水质多为重碳酸盐钙镁型,水的硬度大(所以患结石者较多),呈弱碱性,这不但会使茶黄素自动氧化而部分损失,而且会影响茶叶有效成份的溶解度。由于当时没有水处理技术,显然,这无疑也是“汉茶”不受青睐的原因。 + K4 E$ ]' d( |. r F0 U* G
- ^6 ^4 {- B8 e" Q6 J9 m 由此可见,《茶经》将汉中列为最差的茶区,不但是唐代与当前气候差异影响使然,而且与汉中弱碱性硬水水质有着重要关系。今天,在评茶活动中采用相同的软水泡制,中国各大名茶的产区和《茶经》中的著述多不吻合,汉中绿茶在全国性大赛中金奖累累,这也进一步佐证了上述观点。
8 d4 K% E5 t! t0 C0 }6 x0 y$ |2 y( U; C' s/ H2 g, H5 |/ F- O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今后我们完全可以采用以上这些理由底气十足地来直面这个问题。而且,汉中作为“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历史底蕴厚重,生态条件优越。刘邦、张良、张骞、张鲁、诸葛亮等文化资源足以赋“汉茶”予浓郁的人文气质,朱鹮、大熊猫、金丝猴等国宝级动物共栖地的生态资源足以赋“汉茶”予坚实的环保优势;于是“人文有机名茶”的高端品牌诉求便顺理成章。 (楚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