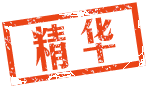@ME: 
|
说到汉中的山水,汉山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这倒不是说汉山有多么的挺拔抑或峻秀,而是因为这座海拔仅有1470米的山体,在远古就有记载。《诗经·大雅·旱麓》中的旱麓,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汉山。
现在的人们无法去景仰远古的汉山,但我们可以凭借文字的魅力,想象当年汉山的情景。“瞻彼旱麓,榛苦济济。岂弟君子,干禄岂弟。”我们不难发现,昔日的汉山,榛树苦树和乐共生,一派繁茂的胜景。
我想,对于昔日政治的是否清明,或许正史和野史都会有人为编修的痕迹,但汉山原生态的富饶美丽,怕是任何一个史官都不愿去篡改抑或删繁就简的。这作为一个独立的山体,汉山是荣幸的;而作为一方百姓,生于斯长于斯的古人也是荣幸的。
今天,我们登临汉山,不得不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当年周国的使臣,来到汉中,独独选择了汉山作为宣喻政教祭祀的道场?为什么周国把国家的强盛、人才的辈出和汉山茂密的森林等同看待?
我们无法去臆想古人的思辨,但我们可以检视今日的作为。汉山屹立在汉水冲积的平川之上,俯瞰肥沃的汉中盆地,山体上田垄层叠,绿树成荫,溪水缠绕体表,真可谓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也就是说,山是树的载体,树和水又是山的血液,汉山丰沛的自然资源,在历朝历代都含情脉脉地滋养着这儿的人民。
我们看到,汉山高高的耸立,打心眼里就有一种自豪感。远望汉山,只见它突兀、雄浑、硬朗、壮阔。它高高地矗立,与城镇阔街高楼互为背景朝夕相伴。汉山之巅名为“大顶寨”,却并不似其他名山一样遍布庙宇道观,它是一座只属于世俗凡界的名山。百姓靠它看天气;汉山戴帽,大雨快到。政府靠它转播电视,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在山顶上建起了电视转播塔。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唯有汉山之巅灯光闪烁,方圆数十里可见,它的灯光让汉中人感觉到无比的塌实和温暖。风雨历练,汉山在不知不觉中就已成为人们心里的某种仰承。
汉山是汉中人的福祉,也汉中第一网的心灵家园。春天的汉山妩媚多情,山坳中,梯田里,黄灿灿的油菜花与山间青黑的矮松、白亮亮的冬水田一起,组合成一幅明媚艳丽的水墨画。夏天的汉山壮美辽阔,山脚下绿稻千重,山腰间青松翠柏,绿枝拂面,山顶上白云悠悠,蓝天高远。秋天的汉山饱满成熟,山体红遍,层林尽染,农家篱笆外果香弥漫,屋顶上炊烟袅袅,野菊花肆意地开放,“救兵粮”缀满枝头,红得耀眼。冬天的汉山纯净质朴,山涧里溪水清冽,山路上黄叶满径,山尖处薄雪覆顶,倦鸟归巢,万籁俱寂,一片肃穆安宁。
我曾经把汉山比喻成父亲,它对人们的滋养就像父亲在庇护儿女一样,只付出而不需要回报;我也曾把汉山比喻成母亲,它那一草一木就像母亲的一针一线,惠及儿女胸藏博大的母爱。其实,反复地体认汉山,我发现我的比喻都有失偏颇。汉山,它的刚挺,它的柔情,它的不老的精魂,是任何比拟都无法巨细的。汉山,它就是它,坚实地屹立在我们的身边。
因而,不管我们出于何种动因,我们登临汉山,我们想登临山的最高峰,终究也只能以敬畏的方式与山峰望守。假如有人想征服,在我看来,他不是太浅薄,就是太张狂。
(汪银泉)
|
|